【交锋】扰乱法庭秩序罪是否会被滥用
发布时间:2015-07-08 来源: 法制日报 点击:
次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再次就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进行研究。在该修正案中,有关对扰乱法庭秩序罪条款的修正意见备受社会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的关注。有人认为这一条款体现了立法技术的进步,也有人认为这一条款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而这样的争论也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刑法修改的真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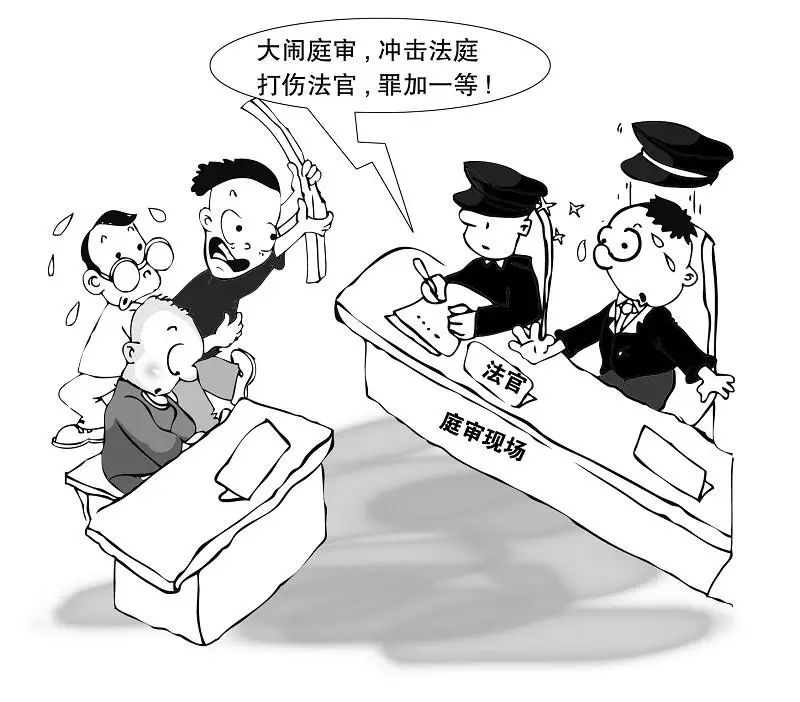
扰乱法庭秩序罪,在1997年刑法修正后才首次出现。此前,如果庭审中出现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案件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应按照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进行定罪量刑。必须肯定的是,1997年刑法通过增设“扰乱法庭秩序罪”来惩戒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更有针对性,也更有利于刑法分则罪名体系的完善。
1997年刑法修正,在妨害司法类罪名下专设“扰乱法庭秩序罪”,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等两种行为予以有针对性的刑法规制。从刑事立法技术角度看,该条款采取非分类列举的普通表述形式,对上述两种行为达到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程度时,予以定罪处刑。这种立法形式的优点在于历史承接性强、便于司法人员理解和适用。
然而,该条款修正前的缺点也正是在于表述过于简短,逻辑性、严密性及针对性均有待加强。比如,未将殴打诉讼参与人的行为纳入到打击对象中来,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矛盾比较尖锐的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在情绪激动之际向对方当事人当庭施暴的极端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当司法实践与制定法之间出现供求不对称之时,再次修正就成为必然之举。
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正,呈现出立法技术上的三个新变化:一是以“列举+兜底”的立法形式提高该罪的实践针对性和适用范围。此次修正最大变化,就是明确列举出三种扰乱法庭秩序的具体行为,再配套一项兜底性条款,以求最大限度满足司法实践需要。二是以具体行为表现扩容的方式有效应对近年来维护法庭秩序面临的新障碍。此次修正增加了“殴打诉讼参与人”“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且不听法庭制止的”两种具体行为表现内容,弥补了原有条文在内容上的欠缺,提升其实践适用性。三是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效对接。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以及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均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以及诉讼参与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进行了专门规定。在程序法已经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刑事实体法进行修正对接也是立法的必然举措。
从刑事立法技术的角度,以“列举+兜底”为表现形式的条文绝非个例。如果采用列举式立法形式,逻辑上必须要求配套兜底式条款,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具体个罪条款的实践适用能力,造成立法虚置。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正,是以维护司法权威为主旨、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严重扰乱法庭的种种新表现进行的立法完善,同时也是出于联结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条文内容的客观需求。因此,从刑事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对“扰乱法庭秩序罪”条款的修正是完善刑法体例与内容的具体环节,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自我发展与提升的客观趋势。作为司法工作者,笔者衷心希望该罪名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进一步研究与审议中,最大限度地吸取合理意见,字斟句酌加以全面完善,最终为提升我国司法权威和法庭威严发挥应有作用。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第三十六条,准确地说,是该条的第(三)(四)项存在被滥用的风险。特别是第(四)项,这种“口袋罪”的设定历来就是法律滥用的重灾区。
依照第(三)项的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该项规定看似清楚明白,然而对刑辩律师而言,却好似雷区。
为什么这样讲?我想这大概和刑事辩护工作本身的特点脱不了干系。很多时候,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重点主要还是对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及公诉人所发表的公诉意见提出否定和质疑。而这种否定和质疑或多或少的、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办案人员取证工作及公诉人所主张观点的否定性评价,有的时候,这种否定性评价还会波及到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个人。
正是这种“特定情况下”的形式上的近似性有可能会给滥权者以可乘之机,从而将刑事辩护与“侮辱、诽谤”画上等号,将辩护律师对控方证据、观点的质疑,视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侮辱、诽谤”。如果这样的可能成为现实,并不幸被复制,那么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无疑会对刑辩律师较为不利。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不可能排除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发生,针对此类行为的处理,律师法及现行刑法第三百零九条均已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现行的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之规定,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由此可见,现行法律规定不仅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制,且法律针对不同行为设定多样化的处罚措施,也较好地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过的基本处罚原则。毕竟,与“冲击法庭”“殴打司法工作人员”这类具体的肢体行为,以及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造成实际侵害或现实危险的行为相比,所谓的侮辱、诽谤、威胁等言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要小得多。
然而,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六条却将上述这些社会危害性具有明显差别的行为一律视为“扰乱法庭秩序罪”。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将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行为犯罪化。
作为律师也作为公民,我们愿意遵纪守法,也愿意服从并尊重法庭,我们不惧怕,也不逃避合法、合理的监督和管理。但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三十六条模糊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根据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十条之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可见,“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已是一项国际公认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对律师权利的保障,更是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在强化人权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律师的作用和意义更应当得到肯定和尊重,切勿以个别“控辩冲突”“辩审冲突”为由,将律师置于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六条第(三)(四)项的追责之列。
(融媒体新闻中心编辑)
(责任编辑:郑源山)


